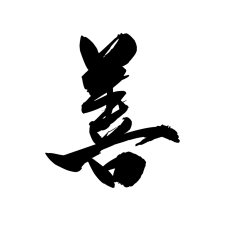作为宋明儒学殿军的蕺山学何以成立 ——以“本体与工夫”之辨为视角
摘要:宋明儒学发展至王阳明心学,“本体与工夫”之辨凸显为儒学的核心话题。王阳明本人侧重于本体,取消了工夫的独立性。王门后学中,泰州学派消解了本体,失落了工夫;江右王门将良知本体向内收摄,在工夫修养上回归程朱。明末刘蕺山通过改造“慎独”、“诚意”、“立人极”、“迁善改过”等传统话语所产生的一套新论,将“本体与工夫”之辨发挥到理论极致。由此,作为宋明儒学殿军的蕺山学方得以成立。
关键字: 本体与工夫;慎独;诚意;立人极;迁善改过
明末大儒刘宗周(1578—1645,号“蕺山”)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一直被作为宋明儒学的殿军来看待。这与明清之际的黄宗羲(1610—1695,号“棃洲”)和以牟宗三先生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家等人对蕺山学的阐扬密不可分。黄宗羲身历明清鼎革,有感于整理故国文献的必要,因而编次《明儒学案》,有意凸显了同乡先贤王阳明和其先师刘蕺山的地位。牟宗三先生更是通过其发明的“宋明儒学三系说”,将刘蕺山提升到了堪与程朱、陆王比肩的人物。而牟宗三先生的发明,又源自其对宋明儒学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所占地位的判定。牟先生认为:“夫宋明儒学要是先秦儒学之嫡系,中国文化生命之纲脉,随时表而出之,是学问,亦是生命。自刘蕺山绝食而死后,此学随明亡而亦亡。”[1]可见,黄、牟等人对蕺山学的定位都是在“明亡”这一时代大背景的关照下而展开的。而“明亡”作为一历史事件显然尚不足以界定学术之兴衰,且不论明清鼎革之后,依然存续了众多的理学名臣。究竟作为宋明儒学殿军的蕺山学能否成立,尚有待于对宋明儒学在理论上的发展做进一步的辨析。
一、 “本体与工夫”之辨:后王阳明时代的理论困境
(一) 王阳明的“本体与工夫”之辨
众所周知,宋明儒学的兴起由拒斥佛老之道,重建儒家道统而来。佛老给予原始儒学最大的冲击莫过于夫子所罕言的“性与天道”,儒学的重新崛起势必在此形而上层面与佛老一决高下。因而,宋明儒学在初创时期就受到了佛老问题意识的指引,“北宋五子”在批判佛老的同时,无形之中先接受了对方体用、本末的理论架构,进而才去发掘原始儒学文本中的相关概念表而出之。由此,才将原始儒学所倡导的一整套形而下的伦理观念上溯至形而上的理论根源。这在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1130—1200,号“晦庵”,学者称“朱子”)的“天理”观念中得到了系统的表达。而宋明儒学发展至明代中叶,超越在上之“天理”的过高地位,拉大了与人之现实生存的巨大张力,如此使得天理的权威性受到质疑。为了挽救理学的漂浮无根和人间伦理秩序的合法性,王守仁(1472—1529,号“阳明”)大力表彰与朱子相对的陆九渊(1139—1193,号“象山”)心学,通过“心即理”的观念,将道德本体重置到人心内在的“良知”之上。由此,程朱理学所阐扬的“主敬”、“格物”、“知先行后”等一套面向现实生活界中人伦事物的工夫论,开始有被“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2]所取代之势。众所周知,在阳明学话语中,所谓之“事事物物”,乃是“心外无物”。因而,朱子所理解的“格物”等工夫在阳明这里,一开始就不再是向外的穷究事物之理,而是将工夫致力于人心内在的良知本体之上。
需要辨明的是,“良知”与“天理”相较,虽然没有打破“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体用思维方式,但却使得个体修养层面上的本体与工夫皆统一于良知之上。问题是,就理论建构而言,本体不离工夫,工夫不离本体,如阳明所言“合著本体的,是工夫;做得工夫的,方识本体。”[3]然而,就“致良知”的实际工夫运做而言,必须时刻将做工夫致力于本体之上,如阳明所言“功夫不离本体,本体原无内外。”[4]可见,在“本体与工夫”之辨的问题上,王阳明本人始终强调工夫应当被涵摄于本体之中。就本体与工夫的孰轻孰重立论,不得不言王阳明偏向于本体一边,工夫一边并不具备自存的独立性。
因而,阳明学的理论重心落脚于对本体层面的辨析。而王阳明对心体论说的典型话语可谓是:“无善无恶心之体”。[5]这一话语可分两方面观之:一方面,处于形上界的心体,乃是超越于形下界的万事万物而存在,因而只能采取“无……”这样的句式才足以名之;另一方面,心体本身处于未发之中,在未与事物相接之时,尚不存在善、恶这样的价值判断,否则就无以彰显本体的超越性。所以,“无善无恶”一语既强调了心体的纯粹性,但同时又必须能够为现实生活中各种善恶行为提供理论根源。由此,理论的吊诡之处,就展现为作为超越善恶的心体既要为现实生活中的善行,也要为现实生活中的恶行提供理论说明。而且,从阳明学流变的事实来看,其进一步的发展的确出现了“酒色不碍菩提路”的狂禅路径走向。因而,王阳明本人关于“本体与工夫”之辨所蕴涵的内在可能性,也就成了王门后学在此问题上争执不下的滥觞。
(二) 泰州学派对“本体”的消解
在后王阳明时代,弟子们在“本体与工夫”之辨问题上,产生了极大的分歧。抛开黄宗羲按地域划分的局限,可以将这些弟子划分为两种趋向:一是王门左派,这些弟子执定良知本体人人具足,如王畿(1498—1583,号“龙溪”)的“良知现成说”、王艮(1483—1541,号“心斋”)的“良知日用说”等一任良知本体的发用流行,从而为“满街皆是圣人”大开方便之门;一是王学右派,这些弟子强调良知工夫之难求,如钱德洪(1496—1547,号“绪山”)的“事上磨练说”、邹守益(1491—1562,号“东廓”)的“良知主敬说”、聂豹(1487—1563,号“双江”)和罗洪先(1504—1564,号“念庵”)的“良知归寂说”等在理论上继续深研心体,力图通过工夫的实修来收摄本体之流荡。
王阳明门下在社会上产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王艮的讲学之宗旨在于“百姓日用即道”,所谓“道”不再是高远难求的不变之天理,而只是流行于世俗的百姓日用生活之中。由于其讲学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辨析,因而吸引了大批的灶丁、盐户、樵夫等中下层小市民。王艮将师门的“致良知”做了一个翻转,即“良知致”。[6]且看他如何通过《明哲保身论》赋予良知以新的效用。王艮说:“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所谓不学而知,不学而能者也,人皆有之,圣人与我同也。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保矣。”[7]这里,与其师王阳明相较,作为本体的良知,其发用的能动功能开始转化为保爱一己之身的功利性。《大学》中原本作为家、国、天下起点之“身”,开始从一个德性修养的伦理本位,转化为需要保护珍爱的生命对象。由此,作为先验良知的道德本体义开始淡出理论的关注点之外,反而,生活经验层面的身体利益成为理论的最终归宿点。
沿着这一路向,泰州学派经过颜钧(1504—1596,号“山农”)、何心隐(1517—1579,号“夫山”)诸人再传至李贽(1527—1602,号“卓吾”)已然不再执着于良知之学的话语体系了。以李贽为例,他的思想核心在于“童心”二字:“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8]在李贽的“童心说”中,心学理论的重心已由先验本体之心的存有与否直接转到了后天经验之心的真假问题上。这样的问题转换,意味着作为本体和工夫合一的“心”的观念之中已经去除了良知的本体之义,直接下降到了现实生活中知冷知热的肉团心。相较而言,良知作为未发之心体是无时不在的,元不会丧失;而童心作为随意念而发的初心,则很有可能被后天社会生活中所遭遇的闻见道理而左右,以致丧失。依据现实的生活经验,不管李贽所说的“真心”是作为“童子之心”,还是作为“最初一念之本心”,皆是指作为感官存在意义上的“肉团心”而非道德本体意义上的“良心”。比如,不论是童子还是成人,在面对穿衣吃饭等生存所需之时,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感官情欲的自然流露。在此之时,人心尚未受到外在伦理规范的影响和制约。李贽倡言:“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9]在李贽看来,人心甚至就可以直接等同于私心。阳明学发展到李贽这里,与“天理之公”价值相对的“人欲之私”开始进入儒学的正面话语之中。
(三) 江右王门对“工夫”的贞定
作为王阳明一生精神之所在的江右地区(今江西省),[10]是王学发展的另一重镇。其中主要表现为两大派别:一是邹守益的“良知主敬说”;二是聂豹、罗洪先的“良知归寂说”。抛开两派的区别不谈,就“本体与工夫”之辨问题而言,这两派的共同特征是抑制良知本体的活灵活现,转向注重工夫层面的实修。下面简要述之。
比如,邹守益认为:“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以尘俗也。戒慎恐惧,常精常明,则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故道乘之国,直以敬事为纲领。”[11]可以看出,邹守益强调“良知之精明”虽然不失作为学问头脑之良知的主宰作用,但由于过分注重“戒慎恐惧”的修养工夫却丢失了阳明良知教随感随应的活泼一面。更有甚者,邹守益将“良知”与“敬”字并提,在工夫取向上已然回归到了程朱理学的“主敬”路向之上。
另外,黄宗羲在评价聂豹之学时说到:“先生(聂豹)之学,狱中闲久静极,忽见此心真体,光明莹彻,万物皆备。乃喜曰:‘此未发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从此出矣。’及出,与来学立静坐法,使之归寂以通感,执体以应用。……唯罗念庵(罗洪先)深相契合,谓双江(聂豹)所言,‘真是霹雳手段,许多英雄瞒眛,被他一口道着,如康庄大道,更无可疑。’”[12]其实,根据王阳明的良知教,良知的发用本来是无分动静、未发已发、寂静感通的,但“良知归寂说”明显过分强调了心体向内收敛的一面,或者说,致力于将工夫用在于心体上。这种务内遗外的工夫,一方面进一步将阳明的良知本体推进到人心的隐微之地,另一方面也遏制了良知的发用流行。而这样的理路,得到了明末大儒刘蕺山的进一步发挥。
二、 蕺山学的本体论:“慎独”与“诚意”
(一) 刘蕺山的“本体与工夫”之辨
黄宗羲概括晚明学风到:“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能羁络矣。”[13]可见,晚明时期泰州一派占据着学界的主导地位,从而造成了儒学滑向禅学的空谈学风。对于已然越出儒家名教的“异端”行为,需要在本体与工夫两个层面加以救治。这正是身处晚明末世的蕺山学兴起的理论缘由所在,也是蕺山学建构的理论任务所在。
刘蕺山针对王阳明良知教的流弊,说到:“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亦用知者之过也。”[14]这里的猖狂者指泰州,超洁者指龙溪。猖狂者冲破了伦理规范的束缚,造成感性情欲的泛滥;超洁者脱离了道德实践,过高地强调良知的灵明觉悟,与禅宗的玄悟打并在一起。面对这样的问题,一方面要重建儒家道德本体的庄严性,防止情感的过分渗入所导致的认人欲为天理,另一方面要培养个体的道德自觉意识,将工夫修养切实贯彻到生活的日用常行之中。
面对“本体与工夫”之辨的理论问题,刘蕺山认为:“本体只是这些子,工夫只是这些子,并这些子,仍不得分此为本体,彼为工夫。既无本体与工夫之分,则亦并无这些子可指。”[15]可见,作为阳明后学的刘蕺山在此依然遵循的是王阳明“本体与工夫”两不相离的教诲。但问题的分歧在于,当这种“即本体即工夫”的理路运用到工夫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刘蕺山却与王阳明发生了偏离。与王阳明“致工夫于本体”的侧重不同,刘蕺山有鉴于晚明空谈学风下工夫的丧失,却不得不倾心于在工夫一边寻求着落。在与泰州后学陶奭龄(1571—1640,号“石梁”)的会讲中,陶、刘双方发生了辩论。据“证人社”《会录》中记载:
陶先生曰:“学者须识认本体,识得本体,则工夫在其中。若不识本体,说甚工夫?”先生曰:“不识本体,果如何下工夫?但既识本体,即须认定本体用工夫。工夫愈精密,则本体愈昭荧。今谓既识后遂一无事事,可以纵横自如,六通无碍,势必至猖狂纵恣,流为无忌惮之归而后已。”[16]
观此辩论,陶、刘两者同样认为,工夫为本体所涵摄,不存在本体之外的工夫。但分歧在于,刘蕺山进一步强调的是,本体自身并非完满自足,有待于工夫的精密实修才得以呈现。如果说,不存在本体之外的工夫,那么同样也不存在工夫之外的本体。因而,在刘蕺山看来,“学者只有工夫可说,其本体处直是着不得一语。才着一语,便是工夫边事。然言工夫,而本体在其中矣。大抵学者肯用工夫处,即是本体流露处;其善用工夫处,即是本体正当处。若工夫之外别有本体,可以两相凑泊,则亦外物非道矣。”[17]
如此,本体的发用与否,并不依赖于良知的自觉。反而,本体的实存倒是由现实生活界中具体工夫的实行所证明。正是由于理论与现实的反差,使得刘蕺山开始重新阐释《大学》、《中庸》等经典,并提出了取“致良知”学说而代之的“慎独说”和“诚意论”。
(二) 就“本体与工夫”的合一而言“慎独”
“慎独”思想最早见诸于《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大学》云:“所谓诚其意,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中庸》云:“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18]所谓“慎独”无外乎有两层含义:(1)独处。在不存在与其他关系性角色共处的情境下,即一个人闲居之时,能够保持戒慎恐惧的状态;(2)独知。即使在与其他关系性角色共处的情境下,即大庭广众之中,对于人所不知、唯己所知的事情也要做到“不自欺”。后一种意义上的“独知”在宋明儒学中被阐释为一种与本体论相对的工夫论话语,比如朱子认为:“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着见明显而过于此者。”[19]在朱子这里,要求对于人所不知的几微之事,必须在其念头的发动层面就下工夫克制其中可能存在的私欲。王阳明也结合自己的“致良知”说,认为:“所谓人虽不知而己所独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处。”[20]在阳明这里,致良知工夫的实现与否与个体的道德自觉,即“独知”息息相关。
需要注意的是,与朱子、阳明从工夫修养层面来解释“慎独”不同,刘蕺山“慎独说”的最大特色在于:“独”乃本体,“慎独”乃本体与工夫的合一,并将其视为自己学术建构的核心观念。如其所言,“慎独是学问第一义”。[21]刘蕺山曾在《中庸首章说》中详细阐释了自己的慎独理论,录之如下:
君子求道于所性之中,直从耳目不交处,时致吾戒慎恐惧之功,而自此以往,有不待言者矣。“其”指此道而言,道所不睹不闻处,正独知之地也。“戒慎恐惧”四字下得十分郑重,而实未尝妄参意见于其间。独体惺惺,本无须臾之间,吾亦与之为无间而已。惟其本是惺惺也,故一念未起之中,耳目有所不及加,而天下之可睹可闻者,即于此而在。冲漠无眹之中,万象森然已备也。故曰“莫见莫显”。君子乌得不戒慎恐惧、兢兢慎之!慎独而见独之妙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此独体也,亦隐且微矣。及夫发皆中节,而中即是和,所谓“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也。未发而常发,此独之所以妙也。[22]
由于“独”字本身带有“不睹不闻”、“隐且微”等隐秘色彩,因而极为符合将阳明的“良知显教”(牟宗三先生语)收摄到人心深处的理论要求。刘蕺山正是通过将此内心体察的“独知之地”提升到了本体的层面,从而完成了“独体”的构造。进而,通过自己的“慎独”新论,完成了对《大学》和《中庸》的重新诠释。刘蕺山说到:“《大学》言心到极至处,便是尽性之功,故其要归之慎独。《中庸》言性到极至处,只是尽心之功,故其要亦归之慎独。独,一也。”[23]可见,刘蕺山通过“独体”的观念打并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各自侧重的“性体”和“心体”分离下的不同工夫取向。所以说,“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24]由此,我们也方可理解黄宗羲评价其师的“慎独”之学到:“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儒者人人言慎独,唯先生始得其真。”[25]明确地说,刘蕺山之前所谓之“慎独”是就工夫一边而言,而刘蕺山所谓之“慎独”是就本体与工夫的合一而言。
(三) 就本体的至善而言“诚意”
刘蕺山弟子董瑒(生卒年不详,号“无休”)在编订《刘子全书》时,有按语说:“先生于阳明之学凡三变,始疑之,中信之,终而辩难不遗余力。始疑之,疑其近禅也;中信之,信其为圣学也;终而辩难不遗余力,谓其言良知,以《孟子》合《大学》,专在念起念灭用工夫,而于知止一关全未堪入,失之粗且浅也。夫惟有所疑然后有所信;夫惟信之笃,故辨之切,而世之竟以玄妙称阳明者,乌足以知阳明也哉?”[26]可见,刘蕺山之于阳明学的态度有一个渐变的过程。首先,目睹阳明后学空谈良知,从而对阳明学本身产生怀疑。其次,揭发“慎独”之旨,以达到阳明所倡导的“本体与工夫”的合一。最终,又由阳明后学而反观阳明学本身,对阳明学的核心观念“良知”辩难不遗余力。而刘蕺山晚年的“诚意说”正是为了完成这一理论目的而发。
针对《大学》八条目之一的“诚意”一条,王阳明说到:“《大学》工夫只是诚意”。[27]可见,在阳明学话语中,“诚意”与“慎独”同样属于工夫论层面的修养。阳明又说:“意之所在便是物”。[28]在此,“意”作为心体与外物相接的关联点,属于已发层面。而这些说法在刘蕺山看来,则是有待纠正的。他批驳阳明到:“只因阳明将意字认坏,故不得不进而求良于知;仍将知字认粗,又不得不退而求精于心。”[29]在刘蕺山看来,“意者,心之所存,非所发也。”[30]从而,“意”非已发,而属未发之心体;“诚意”非工夫论,而是本体论。另外,“意者,心之所以为心也。止言心,则心只是径寸虚体耳。着个意字,方见下了定盘针,有子午可指。然定盘针与盘子,终是两物。意之于心,只是虚体中一点精神,仍只是一个心,本非滞于有也,安得而云无?”[31]心中有“意”,“意”为心根,从而保证了心体具有“好善恶恶”的指向功能。若用现代汉语来表述,刘蕺山所理解的“意”就不再是王阳明所理解的“意念”,而是具有价值导向内涵的“意志”、“意向”等义。
因为“意”好善恶恶,因而在本体论上刘蕺山与王阳明对心体的价值判断发生分离。依阳明而言,“无善无恶心之体”,而在刘蕺山看来,心体只有“至善”可说。所以,他认为:“王门倡无善无恶之说,终于至善二字有碍。”[32]在阳明学话语中,因为善与恶作为价值判断只能就心的已发层面而言;而在蕺山学话语中,“意”作为心中之主的价值根源,则决然是好善恶恶的。由此,是“意”而非“心”,才是人之所以为善的本体所在。
三、 蕺山学的工夫论:“立人极”与“迁善改过”
(一) 就工夫的修养目标而言“立人极”
因为刘蕺山的理路是“本体与工夫”的打并合一,因而在对“独”与“意”作本体阐释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慎独”与“诚意”作为工夫论已经获得了新的内涵。然而,“慎独”“诚意”这样的传统话语尚不足以对治晚明的“援禅入儒”运动,刘蕺山在讲学的过程中深感有必要构建一套新的儒学工夫论。
在刘蕺山看来,泰州学派“满街皆是圣人”的口号消除了“圣人”与“常人”之间应有的间隙。从而,使得宋明儒“希圣希贤”的修养工夫失落为“有上截无下截”的狂禅路径。因而重新树立“圣人”这一理想人格在人伦秩序建构中的理想高度,就显得尤为必要。在此问题上,刘蕺山正是通过对理学开山周敦颐(1017—1073,号“濂溪”)“立人极”一语的阐发而完成这一目标的。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说到:“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33]结合周敦颐在《太极图》中所描述的一套宇宙生成论,“太极”本身的阴阳和合造就了宇宙万物的生生之道。天道下贯于人道,唯有圣人方能与天地合德。圣人承担着制定人伦秩序准则的角色,因而圣人乃是人道之极则,亦即“人极”。刘蕺山尤为推崇周敦颐学说,并在其晚年再三修订的《人谱》一书中,仿《太极图》、《太极图说》而作《人极图》、《人极图说》。
但不可简单地认为,刘蕺山只不过是将周敦颐描述的天道运行谱系照搬到人道谱系之中。在周敦颐的《太极图》理路中,由太极、阴阳、五行、万物逐步推演,整个宇宙生成过程自然而然,无需任何外在助力;而在刘蕺山的《人极图》理路中,人极、动静、五伦、百行、成圣,其中始终存在着一种道德自律的“常惺惺”意识。这种道德自律意识尤其体现在成就圣人的最后一步“迁善改过以作圣”的过程中:“自古无现成的圣人,即尧、舜不废兢业。其次只一味迁善改过,便做成圣人,如孔子自道可见。……一迁一改,时迁时改,忽不觉其入于圣人之域,此证人之极则也。”[34]可见,刘蕺山接受了周敦颐“人极”在工夫修养次序上的终极性准则。但刘蕺山强调“自古无现成的圣人”,也就是说,作为“人极”的圣人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并不是完足自存的。“圣人”只是一人格性存在,而且只能存在于理想世界之中。而“人极”之于常人的意义在于,只有当常人将“人极”自觉树立为一理想人格之后,才会生发出道德的自觉。要证人之为人,首先就得立“人极”之大,进而在不间断的工夫践履中方可靠近之。这也正符合了“即工夫而求本体”的蕺山学特色。
(二) 就工夫的修养次第而言“迁善改过”
宋儒在人性论问题上区分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为前者绝对至善,后者可能为恶,由此陷入了人性二本的理论困境。既然刘蕺山重新将心体定位于至善,但何以避免重蹈“气质之恶”的传统话语,他提出了自己的一套“以过代恶”的理论。所谓“以过代恶”,是说在蕺山学话语中,并不存在与“善”相对的“恶”的问题。所谓“过”,只不过是善的缺失而已。
“迁善改过”一语出自《易·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35]在此,“过”无非是指社会交往过程中存在的不合理行为。但刘蕺山对“过”的阐释,带有自己的特色。在刘蕺山看来,伴随着“独体”或“意体”存在着“一点浮气”,此之为“妄”。“妄”乃“藏在未起念以前,仿佛不可名状,故曰‘微’。”[36]此“微过”是后来种种过错的根源。进而,刘蕺山将人在七情、九容、五伦、百行等层面上逐渐展现的不合理行为解释为隐过、显过、大过、丛过等。在刘蕺山“以过代恶”思维中,只有对这些潜存过错的执迷不悟,才最终导致各种现实恶行的发生。用现代眼光来看,“过”与“恶”相较,“过”属于潜意识和意识层面,“恶”属于行为层面。要防止“过”的可能转化为“恶”的现实,就必须在意识层尤其是潜意识层加以对治,所以“工夫吃紧处,总在微处得力”。[37]为此,刘蕺山设计了一套精致的改过工夫:
一炷香,一盂水,置之净几,布一蒲团座子于下,方会平旦以后,一躬就坐,交趺齐手,屏息正容。正俨威间,鉴临有赫,呈我宿疚,炳如也。乃进而敕之曰:“尔固俨然人耳,一朝跌足,乃兽乃禽,种种堕落,嗟何及矣。”应曰:“唯唯。”复出十目十手,共指共视,皆作如是言,应曰:“唯唯。”于是方寸兀兀,痛汗微星,赤光发颊,若身亲三木者。已乃跃然而奋曰:“是予之罪也夫。”则又敕之曰:“莫得姑且供认。”又应曰:“否否。”顷之,一线清明之气徐徐来,若向太虚然,此心便与太虚同体。乃知从前都是妄缘,妄则非真。一真自若,湛湛澄澄,迎之无来,随之无去,却是本来真面目也。此时正好与之葆任,忽有一尘起,辄吹落。又葆任一回,忽有一尘起,辄吹落。如此数番,勿忘勿助,勿问效验如何。一霍间,整身而起,闭合终日。[38]
上述引文又名“静坐法”,为刘蕺山工夫论之具象性表达。从中,可以看出刘蕺山所要求的是通过静坐工夫以实现内心的自我警醒和监察。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不仅不乏宗教性的深刻体验,而且其特异之处在于,此种体验所对治的对象之起点不再是日用生活层面的各种恶行,而是直接面向意识深层的念头过失。且不论蕺山之静坐工夫能否与佛老划清界限,但就其工夫历程的整体性和细节性来看,确是为静坐工夫的修养指明了一现实可行的路径,从而将宋明儒学的工夫论推向了理论的极致。
综上所论,“本体与工夫”之辨乃是由程朱理学中“天理”的高悬与“工夫”的实修之间的过分张力所致。王阳明通过“良知说”将“天理”收摄于人心,完成了本体与工夫的理论合一的同时,取消了本体至善的价值判断和工夫在实践领域中的独立性。王门后学中的泰州学派空谈本体,以至消解了本体,造成了工夫的流荡;明末刘蕺山有鉴于此,沿着江右王门“良知归寂”的理路,将本体与工夫之辨推向高潮。蕺山学在本体与工夫的合一的理路中,通过“独体”打并了程朱理学的“性体”和陆王心学的“心体”;在本体论上,创制了至善无恶之“意体”以修正王阳明无善无恶之“心体”;在工夫论上,重新树立“立人极”的圣人人格,并通过“过”与“恶”的区别构建了一套道德自律的“改过”工夫。正是由于蕺山学在“本体与工夫”之辨的心学语境中,将“本体”与“工夫”两个向度的理论均已发挥至极致,作为宋明儒学殿军的蕺山学方才得以成立。
How can the Jishan School as the last peak of the Neo-Confucianism be established
Liu Hong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Political Academy Wuhu 241002)
[Abstract]As the Neo-Confucianism have advanced to Wang Yang-m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nti and Gongfu became the core topic of Confucianism. Wang Yang-ming focus on the Benti, and cancel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Gongfu. After Wang Yang-ming, Taizhou School eliminate the Benti and lose the Gongfu; Jiangyou School subdue Innate Knowledge to one’s mind and return to Cheng-zhu in the aspect of Gongfu. Liu Ji-shan who lived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uphold the topic to highlight by reforming a set of traditional discourse ,such as “cautiousness”, “sincerity of will”, “being the standard of sages”, “learning the goodness and correcting mistakes”. Thus, the Jishan School as the last peak of the Neo-Confucianism have established.
[Keyword]the Benti and Gongfu; Jishan School; cautiousness; sincerity of will ; being the standard of sages; learning the goodness and correcting mistakes
【参考文献】
[1]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序》,参见《牟宗三先生全集》第8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此外,关于宋明儒学殿军为何人,亦有其他说法。比如,刘述先先生认为,当为黄宗羲。参见刘述先:《黄宗羲心学的定位·绪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但刘述先先生同样承认,黄宗羲为思想史家而非哲学家。本文认为黄宗羲作为刘蕺山之弟子,在思想体系之构造上并不出其师范围,缺乏原创性,故而选取刘蕺山而非黄宗羲为宋明儒学殿军这一说法。
[2]王守仁:《传习录·中》,见《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1页。
[3]王守仁:《传习录·拾遗》,见《王阳明全集》,第1287页。
[4]王守仁:《传习录·下》,见《王阳明全集》,第104页。
[5]王守仁:《传习录·下》,见《王阳明全集》,第133页。
[6]王艮:《年谱·五十一岁条》,见《王心斋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3页。
[7]王艮:《明哲保身论》,见《王心斋全集》,第29页。
[8]李贽:《童心说》,见《焚书·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8页。
[9]李贽:《德业儒臣后论》,见《藏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44页。
[10]黄宗羲:《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见《黄宗羲全集》第7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77页。
[11]邹守益:《简胡鹿崖巨卿》,见《邹守益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507页。
[12]黄宗羲:《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见《黄宗羲全集》第7册,第427页。
[13]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见《黄宗羲全集》第7册,第820页。
[14]刘宗周:《证学杂解》,见《刘宗周全集》第2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78页。
[15]刘宗周:《学言》,见《刘宗周全集》第2册,第404页。
[16]刘宗周:《证人社会录》,见《刘宗周全集》第2册,第507页。
[17]刘宗周:《答履思二》,见《刘宗周全集》第3册,第309页。
[18]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1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页。
[20]王守仁:《传习录·下》,见《王阳明全集》,第135页。
[21]刘宗周:《学言》,见《刘宗周全集》第2册,第396页。
[22]刘宗周:《中庸首章说》,见《刘宗周全集》,第299页。
[23] 刘宗周:《学言》,见《刘宗周全集》,第389页。
[24]刘宗周:《中庸首章说》,见《刘宗周全集》,第300页。
[25]黄宗羲:《明儒学案·蕺山学案》,见《黄宗羲全集》第8册,第890页。
[26]刘宗周:《蕺山刘子年谱》,见《刘宗周全集》第6册,第147页。
[27]王守仁:《传习录·上》,见《王阳明全集》,第44页。
[28]王守仁:《传习录·上》,见《王阳明全集》,第6页。
[29]刘宗周:《良知说》,见《刘宗周全集》第2册,第318页。
[30]刘宗周:《学言》,见《刘宗周全集》第2册,第390页。
[31]刘宗周:《答董生心意十问》,见《刘宗周全集》第2册,第337页。
[32]刘宗周:《学言》,见《刘宗周全集》第2册,第439页。
[33]周敦颐:《太极图说》,见《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页。
[34]刘宗周:《人谱续篇一·证人要旨》,见《刘宗周全集》第2册,第9页。
[35]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36]刘宗周:《人谱续篇二·纪过格》,见《刘宗周全集》第2册,第10页。
[37]刘宗周:《人谱续篇二·改过说一》,见《刘宗周全集》第2册,第17页。
[38]刘宗周:《人谱续篇二·讼过法》,见《刘宗周全集》第2册,第1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