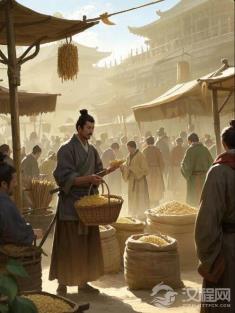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哲学的历史(二)
作者:张再林
就其所处的历史境遇而言,朱子学说当有其无可厚非和不容低估的时代意义。这种时代意义即,在秦汉以降延续千年的“上尊下卑”、“士贱君肆”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朱子学说的推出,标识着士的理性意识的崛起,以及士以之为己任、以之为托庇的“道统”之于“君统”、“政统”的分离和独立。
以朱子为代表宋儒的历史地位乃在于,其经由沙门援佛于儒地从“身”走向“心”,从“外王”走向“内圣”,把孔子所罕言而《孟》、《庸》所独揭的“性与天道”大力发明,并以这一新辟的“谈辩境域”为依凭而为自己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身份,以与曾经不可一世无可匹敌的王权话语相抗衡。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中惟有在宋代人文知识分子即“士”的社会地位才得以真正提升,不仅宋代独开“不杀士大夫”之文治新风,而且宋代皇帝和朝廷“焚香札进士”,其对士的尊崇和礼遇前越汉唐而后逾明清。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中唯有在宋代“以道学自负”的“士”的自我意识才得以空前觉醒,其不仅以公共领域的“天下”而非一己之隅的“家邦”为寄身之所,其不仅振聋发聩地发出了君臣“迭为宾主”,君臣“同治天下”的历史呼声,而且像朱子那样一反中国古代“君子不党”的传统,主张“君子”不但应该有“党”,而且“惟恐其党之不众”,自觉组建以书院、学社为其形式的“精神共同体”、“思想的共同体”,以其同声相应、伟节相望令整个世风为之一振。而这种“政党意识”初萌于洛阳与汴梁之间的对峙,在朱熹的时代随朱学朱
我们看到,也正是从这一全新的“知识论”的取向出发,才使朱子义无反顾地发起了对中国古老的“反求诸身”传统的反击。故当杨时拾孟子余唾主张所谓的“反身而诚”时,不料却遭到朱子的当头棒喝,其谓“万物之理须你逐一去看,理会过方可。如何会反身而诚了,天下万物之理便自然备于我成个什么”(《朱子语类》卷六十二)。同时,也正是从这一全新的“知识论”的取向出发,才使朱子一反中国古人一贯重视躬行的主张,而把所谓的“知先行后”视为当然之则。故朱子提出“夫泛论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中以观之,则知之为先,行之为后。无可疑者”(《答吴晦叔》,《文集》卷四二),提出“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学》先说致知”(《语类》卷一四),以及提出“既知则自然行得,不待勉强,却是知字上重”(《语类》卷一八)。在这里,由于坚持伦理行为的“应当”取决于思维认识上的“必然”,这使朱子的思想既与先秦古人“以履训札”、“以行训德”的思想相去甚远,又与古希腊哲学家“美德即知识”、“恶行即无知”的思想不期而然地几乎如出一辙。
就其所处的历史境遇而言,朱子学说当有其无可厚非和不容低估的时代意义。这种时代意义即,在秦汉以降延续千年的“上尊下卑”、“士贱君肆”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朱子学说的推出,标识着士的理性意识的崛起,以及士以之为己任、以之为托庇的“道统”之于“君统”、“政统”的分离和独立。
以朱子为代表宋儒的历史地位乃在于,其经由沙门援佛于儒地从“身”走向“心”,从“外王”走向“内圣”,把孔子所罕言而《孟》、《庸》所独揭的“性与天道”大力发明,并以这一新辟的“谈辩境域”为依凭而为自己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身份,以与曾经不可一世无可匹敌的王权话语相抗衡。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中惟有在宋代人文知识分子即“士”的社会地位才得以真正提升,不仅宋代独开“不杀士大夫”之文治新风,而且宋代皇帝和朝廷“焚香札进士”,其对士的尊崇和礼遇前越汉唐而后逾明清。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中唯有在宋代“以道学自负”的“士”的自我意识才得以空前觉醒,其不仅以公共领域的“天下”而非一己之隅的“家邦”为寄身之所,其不仅振聋发聩地发出了君臣“迭为宾主”,君臣“同治天下”的历史呼声,而且像朱子那样一反中国古代“君子不党”的传统,主张“君子”不但应该有“党”,而且“惟恐其党之不众”,自觉组建以书院、学社为其形式的“精神共同体”、“思想的共同体”,以其同声相应、伟节相望令整个世风为之一振。而这种“政党意识”初萌于洛阳与汴梁之间的对峙,在朱熹的时代随朱学朱
点击展开查看全文
展开全文
APP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