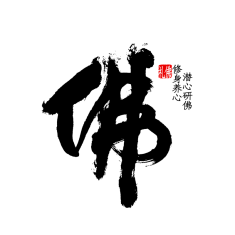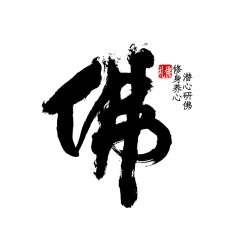佛教对中古文人思想观念的影响
【内容提要】
佛教自两汉之际输入中原后,即对中国中古文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时空观、人生观、死亡观方面给中古文人以全新的观念、思想和境界,促进了中古文人对人生价值的反思和探求,同时拓展了文学创作的思维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原有文学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 佛教 中古文人 时空观 人生观 死亡观
佛教自两汉之际输入中土后,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三大支柱(儒、释、道)之一,对中国近代以前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汉魏六朝是佛教在中国的第一个发展时期,其发展不只是靠印度、西域来华僧人和本土僧人的努力,同时也依赖于中国文人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中国文人对佛教的青睐,使得佛教的诸多观念对文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拓展或丰富了文人的思维空间,促进了中国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
一
古代天竺雅利安人的思维方式极其活跃,他们不受约束、自由奔放、富有想象,有着极为广阔邈遥的时空观念,神话、宗教特别发达。雅利安人所奉的经典《吠陀》就充分展现了他们那自由驰骋、上天入地、无边无际的想象世界。之后,进一步宣扬婆罗门教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以及史诗,更将宇宙、社会、人生紧密结合于一起,把现实的经验世界提升到了想象的超验世界之上,把经验世界的诸种概念无限度地放大或缩小,从而构建出了一系列丰富、奇特的多维境界。
佛教创立时,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婆罗门教及史诗中的时空观念,并有巨大的创新。在空间观上,佛教从佛法广大无边、无所不在的理念出发,把人间的佛教竭力推向了无限绵邈辽远的宇宙之中,架构了凡人难以想象的宇宙立体空间论。这主要体现在“三千大千世界”和“三界”以及各种佛国净土的说法上。佛教认为,以须弥山为中心,以铁围山为外郭,同一日月所照的四方天下构成一“小世界”;一千“小世界”为一“小千世界”;一千“小千世界”为一“中千世界”;一千“中千世界”为一“大千世界”。合此小、中、大三种“千世界”,即为“三千大千世界”。据《长阿含经》卷一八,须弥山高84000由旬 ① ,其至外围铁围山的半径为601725由旬。可见这一“小世界”之高之阔。比照现代天文学的说法,如果佛教的这一“小世界”可视为宇宙中的一个太阳系的话,那么“三千大千世界”则已囊括了太阳系、银河系,向着更为广阔的宇宙空间扩展。“三界”是在“三千大千世界”空间观下建立的向微观深入的立体结构。据《俱舍论》卷八,佛教由低到高把世俗世界分为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认为有情众生均在此三界“生死流转”。他们把色界和无色界各分为四个层次,而把重点则放到了欲界之中,分为六个层次,又称六道:即由低到高依次为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这六道中,重点又在两头,即地狱和天。前者分为十八层或三十层,后者分为六层。这样一种多层次、立体交叉型的三界结构,把向外扩展的空间观浓缩到了人类居住的环境
佛教自两汉之际输入中原后,即对中国中古文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时空观、人生观、死亡观方面给中古文人以全新的观念、思想和境界,促进了中古文人对人生价值的反思和探求,同时拓展了文学创作的思维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原有文学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 佛教 中古文人 时空观 人生观 死亡观
佛教自两汉之际输入中土后,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三大支柱(儒、释、道)之一,对中国近代以前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汉魏六朝是佛教在中国的第一个发展时期,其发展不只是靠印度、西域来华僧人和本土僧人的努力,同时也依赖于中国文人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中国文人对佛教的青睐,使得佛教的诸多观念对文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拓展或丰富了文人的思维空间,促进了中国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
一
古代天竺雅利安人的思维方式极其活跃,他们不受约束、自由奔放、富有想象,有着极为广阔邈遥的时空观念,神话、宗教特别发达。雅利安人所奉的经典《吠陀》就充分展现了他们那自由驰骋、上天入地、无边无际的想象世界。之后,进一步宣扬婆罗门教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以及史诗,更将宇宙、社会、人生紧密结合于一起,把现实的经验世界提升到了想象的超验世界之上,把经验世界的诸种概念无限度地放大或缩小,从而构建出了一系列丰富、奇特的多维境界。
佛教创立时,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婆罗门教及史诗中的时空观念,并有巨大的创新。在空间观上,佛教从佛法广大无边、无所不在的理念出发,把人间的佛教竭力推向了无限绵邈辽远的宇宙之中,架构了凡人难以想象的宇宙立体空间论。这主要体现在“三千大千世界”和“三界”以及各种佛国净土的说法上。佛教认为,以须弥山为中心,以铁围山为外郭,同一日月所照的四方天下构成一“小世界”;一千“小世界”为一“小千世界”;一千“小千世界”为一“中千世界”;一千“中千世界”为一“大千世界”。合此小、中、大三种“千世界”,即为“三千大千世界”。据《长阿含经》卷一八,须弥山高84000由旬 ① ,其至外围铁围山的半径为601725由旬。可见这一“小世界”之高之阔。比照现代天文学的说法,如果佛教的这一“小世界”可视为宇宙中的一个太阳系的话,那么“三千大千世界”则已囊括了太阳系、银河系,向着更为广阔的宇宙空间扩展。“三界”是在“三千大千世界”空间观下建立的向微观深入的立体结构。据《俱舍论》卷八,佛教由低到高把世俗世界分为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认为有情众生均在此三界“生死流转”。他们把色界和无色界各分为四个层次,而把重点则放到了欲界之中,分为六个层次,又称六道:即由低到高依次为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这六道中,重点又在两头,即地狱和天。前者分为十八层或三十层,后者分为六层。这样一种多层次、立体交叉型的三界结构,把向外扩展的空间观浓缩到了人类居住的环境
点击展开查看全文
展开全文
APP阅读